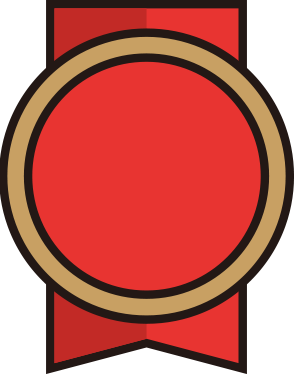晚安,這裡是M的深夜慾望時光~~~
其實這篇還真是臨時寫的,主要原因是下午悠奈丟了個新聞連接給我。

這個是TBS新聞專題,講述的是大家熟知的歌舞伎町治安較差點之一的「トー横」和在那裡聚集的少女們。
很湊巧我剛好也看到常看的粉絲頁轉貼了這個,悠奈看到我的回覆也略微驚訝。「誒居然這麼巧?看來你今晚又有故事寫了。」
「妳不也是有段時間待在那裡嗎?剛上京的時候。」
悠奈聽到我這麼說直接大笑起來:「哎呀呀,都過去了。」
咱且先說說「トー横」是什麼。 首先「トー横」指的是聚集在東寶大樓週邊的年輕人,少年少女都有。這些少年少女會流連在這裡有著各種理由——被家暴、被排擠、被父母逐出家門、對人生失望透頂⋯⋯而在推特、line等sns系統的散播下,這些少年少女就聚集在這裡。
人就這樣群聚起來,有些人甚至拉著行李逃家——帶著行李箱的少女在這裡反而相當普遍。也因此大多數會遇到的「家出少女」都幾乎會在這裡出現。

「妳怎麼會那麼突然給我看這個?」我趁著下午茶時間發了個信息給悠奈。
「啊剛好這幾天我看到Youtube的TBS頻道把這個放上來就和那傢伙一起看了。而且現在這些人不僅僅在トー横了,已經擴散到新大久保區域了喔。」
新大久保?「誒差不多十分鐘的路程耶,怎麼會跑到那邊去?」
悠奈無奈回答我:「人越來越多了當然就越走越遠啊。」
人越來越多?「嘿啊,東京就像黑暗中的燈吸引一大群飛蛾一樣。但就算是容納的再多,那裡終究還是會飽和的,因此沒有位子的人聚集的地方開始就會往附近移動。新大久保既靠近又方便和同僚碰面,自然而然就變成新的聚集地了。不說了,晚上聊。」
晚上悠奈找我聊天繼續下午的話題。日本友人趁機露了個頭看著我。「還沒死喔?」
「我死了你要繳奠儀嗎?」
「我包一千萬給你。印尼盾。」
一說完我秒豎起中指看著他:「少廢話啦,你現在不是該摸摸她的頭嗎?」
「我在摸啊,不只頭還連帶大腿呢。」
聽到這裡我就看到悠奈超無奈的看著日本友人:「摸歸摸但不要摸到別的地方去好不好?」
「妳可以繼續跟他聊啊。我摸我的又沒關係。」
「不要鬧啦!」悠奈直接一拳擂在日本友人肚子上後看著我:「看著他們我就想起了このみ呢。她現在不知道在哪呢。」
「香海嗎?我也沒辦法聯繫上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呢。」我無奈的嘆氣。畢竟悠奈和我口中說到的香海,就是在這裡流竄的人當中屬於悲慘世界的那一類人。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香海的時候是坐在悠奈身邊,一臉警惕。「誒這個人能信任嗎?」
「安啦,我現在飯票的朋友,而且妳只要把妳的事情說出來就有錢了喔。」悠奈一臉信心滿滿的表情看著我:「對不對?」
「對對對,但妳們說話的速度不要太快,翻譯器沒那麼敏銳。」我說完後對面的香海一臉驚訝:「誒?!外國人?」
「對啊,會聽一點日文,但不是很精通的那種。」
「啊這樣的話我說慢點。」香海看著我:「但是你得給我錢喔。」
「我給你Amazon Point還是其他什麼的OK嗎?」
「嗯⋯⋯你給我Amazon Point吧,我直接折抵現金給她——畢竟對她來說現金比較重要。」悠奈說完後我啥都沒說馬上打錢給她,五分鐘後⋯⋯「誒,三萬?!」
悠奈詫異的看著我。「妳看她手臂上的傷痕就懂了——我覺得她的故事就值這個價。」
「誒~~好好喔。3萬的話我可以活一個月耶。」香海看著我一臉感激:「我好久沒有一口氣拿到1萬以上的錢了。」
「那麼慘!?等等,妳從哪來的?」我詫異的問道。「嘛,你知道栃木嗎?我的老家在那裡。不過我現在其實算是逃家模式。畢竟我如果不逃的話⋯⋯會有點危險。」
危險?「她家的情況有點特殊——簡單來說就是爸不疼媽不愛的那種。」
「家暴類?」我瞬間明白為什麼要逃了。「方便問一下年齡嗎?」
「我⋯⋯15歲。」
等等,15歲?「等下,妳現在逃家多久了?」
「三個月。這次是第二次逃家——距離上一次逃家已經是半年前了。」香海看著我的眼神除了疲憊外還帶著恐懼:「我是單親家庭出身——父親在我還小的時候就已經不在家裡了。所以我是跟著媽媽一起長大的。」
「媽媽那邊是直接不管了嗎?」
「啊,直接不管了。」香海邊說邊趴伏在桌子上:「女人嘛,帶著一個小孩子要討生活其實是很難的——一旦找到了相好的話,拖油瓶就是阻礙了。所以我勉強把小學唸完進了國中。但是你也知道女生一旦進入了發育期,身體的發育就會引誘其他人的犯罪慾望。」
聽到這裡的我大概猜到了。「老媽的相好盯上妳了?」
她點頭:「嗯,第一次逃跑的時候我只來得及拿手機和錢包——而且還是沒錢的那種。所以逃的不遠最後被警察送回來的。」她說完後直接大笑:「你知道我媽看到警察上門的時候第一句話說什麼嗎?『我們家女兒給你們添麻煩了。』,明明就想把我這個拖油瓶給快點丟了,反倒是她的相好看著我一臉惡意散發出『隨時都能搞定妳』的氛圍,我當下真的驚恐。」
「然後就準備逃跑?但是你沒跟老師說嗎?」我邊聽邊咬著手指——這不跑就會變成母女丼的情況最好能躲就躲。「學校?別鬧了,除非是熱血教師不然沒人會熱心協助的——這種事情就算是輔導課的人把我們這些逃家孩子送回去,只要監護人保證不會再犯的話就不會過問。要逃就是自己想辦法的。所以我盡可能的搞到一點錢,然後想方設法躲開那個男人後,趁著某個夜晚媽媽和他不在家的時候直接拉了行李就馬上逃跑。」
「然後就一路逃到東京?」
「對,不管在Line還是推特上都會有這類型的群組。她/他們會教妳如何到トー横,在這裡大家都是同病相憐,同進同出的那種——只要大家聚在一起,誰都沒辦法欺負我們。」香海說到這裡看著我:「你知道我們在トー横最快的賺錢方法是什麼嗎?男生會去找一些日結工;女生當然就是靠一些⋯⋯你懂的。」

「所以我這時間上找到妳算是幸運嗎?」我總算能擠出笑容。「嘛如果今天沒有跟你聊天的話,我大概就是要露宿街頭了。」香海說完直接大笑:「謝謝恩人聽我說故事,但希望我們以後不會再見。」
自從那次對話結束後,香海就從我和悠奈的生活中消失了。
悠奈不是沒去過トー横試試看能不能遇到香海,但那邊的人輪換太快根本就找不到人直到現在我和悠奈聊起。「希望她一切平安。」我喃喃說道。
「我也希望。」悠奈說完後就下線了,就在我以為只是偶爾提起的事情時,兩個星期後日本友人突然訊息我。
「悠奈本來想找你聊點事,但我覺得她應該沒辦法好好跟你說,我就來當個傳話人吧。」日本友人深呼吸了一口氣後,大概說了一下情況。
我聽完後直接捂臉,然後深深呼吸後看著日本友人:「你去安撫她吧。」
「不想知道實際情況?」
「不想。至少現在不想。」
之後日本友人就跟我聊了トー横現在的情況:
疫情結束後トー横群聚的人其實越來越多,問題也越來越多。「疫情時候晚上八點清場大家就打游擊,現在開了反而更亂。」
因為人越來越多大白天就會開始鬧事,打架起來就是毫無顧忌。

(因為男性而爭風吃醋直接就在トー横開始打起來的事幾乎天天上演)
群聚在這裡的人無所事事就開始嗑藥——有錢有門路的就會嗑草(大麻);沒錢的人就會跑去買強效的感冒藥服用,讓自己昏昏沈沈。
而女性在這裡為了生存,出賣肉體是她們唯一的方法——就算是未成年也一樣。
直接在トー横的周邊變成了站街的女生超多,雖然有著未成年性妨害法的情況,但依舊還是有不少人鋌而走險。
甚至於トー横無法容納的情況下範圍直接擴大到開頭提到的新大久保。「那邊現在不只トー横少女,連職業的風俗女都跑去那邊了。」
日本友人邊說邊喝著啤酒。「她們去那邊幹嘛?搶生意?」
「與其說是搶生意倒不如說是去看看自己多有魅力吧。」日本友人直接大笑:「她們會在乎10000塊兩小時?就是去那邊站街看看自己能拿到多少的Offer後回店裡試試看能不能抬一點價啦!」
「齁那麼熟,最近沒少跑吧?」
「跑來幹嘛?我家這個那麼『好玩』,幹嘛跑出去拈花惹草?」日本友人說到這裡直接看著我:「你如果來東京的話,トー横附近的酒店最好別訂。太亂了。」
「我會訂別的地方啦!」
トー横的年輕人要的是什麼呢?其實到現在我也不知道。
記得香海說過一句話:「其實我們只是想要在狹窄的夾縫中找到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容身之地——能夠讓我們自由呼吸的土地。現在對我們來說トー横就是這樣的地方。如果能夠活到十年後或許我早就離開トー横,也可能沒有。但現在トー横就是我們這種人唯一的容身之地。毫無疑問。」
或許對她們而言,這狹小的廣場如同應許之地一般,在這裡可以無憂無慮的做想做的事;得到久違的快樂和幸福——縱使它實際上是個地獄。
就算是地獄,也是幸福的地獄吧?
以上~M的深夜慾望時光結束~
喜愛的東西很多不及備載
之後會在紳夜食堂頻密出沒,敬請期待




.gif)
.gif)




.gif)